4.3.2 文化景观改造
“景观”不仅是一种地理形态,更是一个“文化过程”[73],是人—地之间互动的产物。景观是社会集体记忆的凝结和物质载体,也是地方文化的可视载体,是地域最直接的文化表征,展现了文化的表层显性内容。文化景观具有传播文化符号的功能,因此可以将之视为“文本”,作为解读地方历史、权力话语、社会符号的重要素材[74]。在旅游发展和空间改造过程中,设计建造者借助这些文本,再度表达出其背后的意义,这种再度表达的过程就是表征,也称为再现。
在以往的发展中,钱岗古驿道周边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基本被闲置,当地社区较少意识到其价值,政府及规划者建构自身对旅游的想象,推动了空间的商品化和符号化[75]。在钱岗古驿道中,为实现钱岗古驿道的保护与开发,当地政府强化古村及村内文物单位修缮和保护,对钱岗古村和钱岗古驿道周边村落沿线遗存进行全面调查,结合环保部门每年60万元的环保专项资金,对全区古村落进行整治;以提升区域景观形 象和空间环境质量为目标,依托钱岗古村的历史人文资源、古驿道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钱岗糯米荔枝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源和沙溪水周边生态景观,整体规划、优化组织公共空间和特色资源,改善人居环境;通过省道118线拓建工程,进一步完善 钱岗示范段的交通设施建设和的配套完善工作。公共道路的修建和整改为旅游业的发展 提供了硬件基础,也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社区民居、公共建筑、祠堂等物质实体的修建形成符号化表征,被展示于村落景区的公共空间。位于景区入口与的古驿道小镇游 客服务中心承担着公共空间和旅游咨询的双重功能,对游客而言这是一个全面了解钱岗古村和钱岗古驿道的绝佳途径,而傍晚时分游客逐渐减少,游客服务中心成为社区居民休闲锻炼的去处,成为邻里日常唠家常的场所。

由此可见,政府通过对社区文化景观的改造与重构,进行可治理空间的物质实践,形成“钱岗古驿道文化遗产”的品牌形象,并通过这些物质实体的修建规范社区居民行为,向居民传达政府意欲发展旅游业、加强社区管理、促进社区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意图。改造前的文化景观是当地社区历史文化的沉淀,是在地方经过历史发展生产出 来的产物,而改造后的文化景观是符合现代社会的、符合政府想象和旅游规划开发目的的景观。另一方面,在这种可治理的空间中,焕然一新的景观、现代化的社区改建、截然不同的标志物使得当地社区居民有着全新的体验,也极大地改变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实现身份的重构。
4.3.3 文化品牌营造
广东省政府建构了“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文化品牌,并采取本体修复、文化显性 表达等方式推动其建构。从化区及村政府响应省政府的号召,积极推动古驿道文化品牌的建设,塑造其文化内核,通过节事活动、赛事活动的举办,为文化表达提供载体依托,并形成文化品牌营造的部分。
“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南粤古驿道汽车定向大赛(广州从化站)、南粤古驿 道航空定向大赛(广州从化站)、粤古驿道徒步健身大会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特色的、长期的文化品牌了,还有很多在特定节点举办的节事活动如南粤古驿道广州从化北回归线夏至日拜太阳仪式、广州从化古驿道自驾骑行摘荔节启动仪式等,这些活动都很好地 提高了南粤古驿道的知名度,也成为从化地方形象的组成部分之一了,为我们本地的经 济发展、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A-01)。“除了通过举办各类节事活动和赛事,我们还设计了“古道君”作为从化古驿道形象大使,它的原型就是从化本土设计卡通动漫的设计师,有着很好的寓意,有利于促进文创理念的盛行,凝聚古驿道内核”(A-02)。
网络媒体配合官方发声,响应政府驱动,向公众传播南粤古驿道的文化价值。多个宣传平台如微信、微博、官网的建立并定期发布相关讯息,为古驿道文化传播提供现代化渠道;钱岗古驿道书稿、主题曲、小品、画册、微信表情包等文化作品相继创作完成,其中《从化掌故》一书,从沿革与地理、胜迹胜景、人物、风物、红星闪耀、从化战事、传奇故事、民俗文化等8个方面,集中整理出古驿道上200 多个小故事,为古驿道历史、文化内涵等要素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媒体平台力量的介入进一步为社会层面非国家行动者的广泛参与提供了舞台。媒体的宣传推广为古驿道文化和形象建构提供了传播平台,形成南粤古驿道实现文化治理重要媒介。政府、学界和市场的力量影响交织,实体层面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抽象层面对文化记忆的塑造,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介入到南粤古驿道“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品牌营造中。
4.3.4 反身性主体塑造
反身性主体即是顺应治理主体意图的自主治理主体,安东尼·吉登斯将现代性的反 身性定义为一种敏感性,“具体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及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受到 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性修正之敏感[76]”。文化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人们能够通过与治理者的反思性协商而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进而实现对人口的治理 这一目标[77]。政府通过文化遗产话语塑造社区主体,治理地方社会,引导居民在思想上加强对国家文化、地方文化的认同,在行动上规范自身行为,从而成为符合当地社会秩序的居民。因此,村规民约等隐性规训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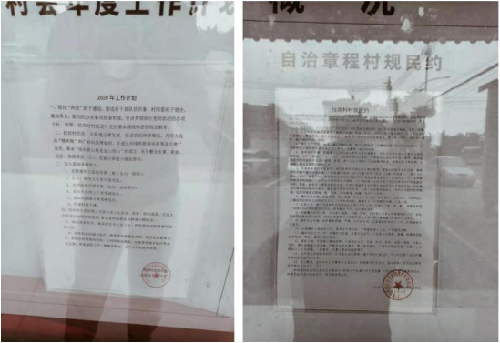
相较于正式制度下的政府管制,村规民约、村庄活动等形式则为钱岗古驿道的村民 提供了非正式制度下的规训,通过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达到反身性主体塑造的目的。钱岗古村将特色小镇建设、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写进村规民约,间接推动了钱岗古驿道旅游产业现代化发展。村规民约规定村民必须支持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如维护建 设乡村建筑景观,新建房屋统一设计风貌,建材应使用石、竹、木等与乡村风貌吻合,建筑色彩、材质应与建筑风格相协调,不得随意破坏原有农村布局等。对于不支持乡村建设发展的,暂停该户本村的优抚政策福利,禁止参与特色小镇民宿、餐饮、特产商店的统一经营。村规民约唤醒村民对家园保护的自主意识,大部分居民对村规民约表现出认可和顺应的态度。
其次,当地政府利用村内公告栏,在社区内张贴海报、公示,引导村民了解政策,以此对钱岗古驿道文化遗产品牌的结构进行知识话语生产;并将村民日常生活与钱岗古驿道文化遗产相联系,使居民加入文化遗产地保护和文化塑造的传承中,使得居民不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维护当地文化品牌形象、增强遗产认知,并在行动进行调整,成为符合政府要求的个体。再次,钱岗古村利用村庄空地,修建公共广场,成为村民茶余饭后 的休闲好去处,在广场中融入钱岗古驿道的起源与繁荣历史,并在村庄旅游核心景区道路两旁以石碑的形式讲述钱岗古村的历史文化底蕴、陆秀夫负帝投海历史事迹及标志性景点,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唤起村民的集体记忆,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形成舆论传播机制,引起村庄内的讨论与传播。这些活动和仪式唤醒了居民对古驿道的记忆,使得古驿道文化显性表达有了载体依托。借助于这些文化活动,古驿道文化实现了传承和不同时空的连续性,并在村民主体中形成了一段绵延的乡村记忆,形成“凝聚性结构”,增进社区文化认同,在潜移默化实现了对村民反身性主体的塑造。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73] 葛荣玲.景观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意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4(4):108-117.
[74] 杨艺,吴忠军.符号与景观:民族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生产研究——基于程阳八寨鼓楼 的田野调查[J].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9,39(04):983-989.
[75] 郭文.江南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30-64.
[7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JM.夏璐,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7] BANG H P. Culture governance: Governing self-reflexive modernit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4, 82(1): 157-190.
相关阅读:
空间生产视角下南粤古驿道文化治理研究(1)(2)(3)(4)(5)(6)(7)(8)
作者简介:
郭婷婷,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中法) 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
(备注:本文为2022年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中法) 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原文收录于2022年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彭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