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间,失掉两位极好的朋友:一位是仲衣,又一位是栗原。他们两位对于教育都有正确的认识,迥异乎时流,而又皆未及尽其所能地披露其所蕴蓄,至这一点已经是教育学术界的莫大损失。仲衣是一位青年运动的骁将,才华焕发,爽直勇敢,很容易得青年们爱戴。栗原则汪汪大度,至诚至明,感动青年们深而且久,确是一位导师,名副其实的导师。

图为林砺儒。
八月十日晚上,我才回到连县县城,在旅馆见着文理学院事务主任杨寿宜君,他头一句话是:“我出来三天了,为要赶来看张先生”。“那一位张先生?”“是栗原先生。他住惠爱医院,昏迷好几天了,现在仅存一息。医师说结核病很深,兼有恶性疟疾,怕没有希望了”。十一日天亮,我渡江赶往医院,看见他僵卧病榻,只还有气息,连呼不应,夫人带着一个小孩在旁边流泪,据说那两个大的孩子留在东陂家里伴着祖母。当天我回去东陂,翌日接到电话,报道他长眠了。
前年和去年夏秋之交,栗原先后犯了两次咳嗽病,去年一次很厉害,直休息了三个多月。今年七月初旬,陈子明先生由东陂出来曲江,说来曲江那一天,他来为我送行,特托我给一个患初期肺病的学生冯桂森买药,那时他精神还好,断料不到潜伏在他自己体内的结核菌正在预备要他的命,我也料不到那回一别便成永诀。八月三日,他往连县就医那天,还留给我一封信,说:这回病不似去年,系主任职务势难继续,若是新任有意留他,只能应聘教席。可见直到那时他还不信自己会死。可是那封信已经是叫小孩代笔的了。
栗原的生死观是严正科学的,追悼他死去,一切流俗的诔辞挽诗都难适用。我回到东陂,对学生们报告他病危绝望的消息,大家都黯然沉默。这“黯然沉默”是最真挚不过的表情,远胜于言语,更远胜于文字。像我的手笔这样笨拙,要发表情感或追述一位亡友的人物,更有点不自量力。然而心里又觉得不能不写,只好想到什么,便写什么。
我和栗原真正订交,始自他来勷大教育学院任教席,那时抗战军兴还未久,学院迁在梧州,他直来到苍梧。开课之后,一个星期日,他来我寓所谈话,彼此交换教育的见解,很融洽,很愉快,直谈论了整个上午。那时使我想起初会仲衣时的情景,而又觉得他的言论更为精细深醇。现在试把当时谈话的结果大略回忆一下:
廿年来,我国教育学术界很热闹地输入舶来的教学方式或教育技术,如什么制,什么法等等,花样时时翻新,遂以为这已极教育之能事,栗原认为这现象殊不佳。他以为人类自文明大启,社会阶级形成之后,教育早变了质而为特权阶级保守原状之具。在我们中国这样长久地停滞于封建文化的社会,教育更显然是士大夫荣身之具,几乎习非成是,牢不可破。一个社会的原有文化若成了它自身生长的桎梏,在那里的教育就必然是自己麻醉,装点门面的勾当,无论仿用什么时髦方法,也不能尽其所应尽的机能。只有快到了革命的转变的前夕,人们才能看见几分教育的本质。我们若能透视教育的本质,便可晓得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里面,只有在革命轰轰烈烈的时期,教育才发挥了几分它所应有的功能。现代的教育学诞生于前世纪初期的欧洲,就因为那时民主革命四起。可是自从欧美革命成功之后,市民们代贵族地主而掌握了政权,又希冀维持他们的地位于万世不易,便消失了革命性,甚至于不惜起用以前他们自己所曾经要铲除的封建残余文化。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教育学便难免夭折,因而现今的教育学实在是未成品,充其量也只能说在要形成之中。我以前说过,近来这样强调地把新教育限于教学方法技术的圈子里,实在是市民教育学者的一种遁辞、解嘲,一种避难所,一种遮眼戏法。栗原对此点很表赞同。因而他以为研究教育科学之建设是今后必需的工作,我们民族抗战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大业,同时就是建设教育科学的极好机缘,关于当时“抗战教育”的呼声,我们都承认这回抗战就是给我们整个民族的最好不过的教育。我提出两句口号:“只要抗战能够教育化,教育就必然地抗战化”。他对此也表示首肯,而补充地说:在抗战期间,教育能否彻底改造,还要看能否够得到两个条件:一是富有魄力的新政治,二是相当充足的教育工作干部。
栗原初治生物学,复治哲学,这样取道于自然科学是研究哲学的最妥当的途径。他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两面的基础都非常坚实,所以他治教育学的态度是很谨严的。近年他起草一部教育哲学,快要脱稿了,而忽告绝笔,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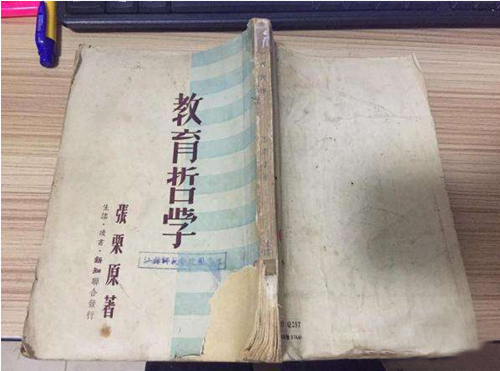
图为张栗原所作《教育哲学》。
抗战以来,青年学生都心情活跃,而又往往烦闷激昂,这是一点民族的生机。我虽不肯放任学生们幼稚的冲动,而也雅不愿拘束他们“埋头伏案”,“安分守己”。因而导师们的工作很要十分讲究,辅导青年们蓬蓬勃勃的生气,不耗费而也决不桎梏,才可得到他们悦服。栗原便是很得力的一个。学生们集团的座谈会、读书会、后方服务工作等等,若得他任指导,没有不皆大欢喜,兴致十倍的。偶然有什么辩论,争执,甚至于闹一下子别扭,一经他出来开导,无不立刻消解。四年之间未曾失败。有过失的学术若经他指摘,也很少有不悔悟的。尤其遇着时局有了变化,或学院也受影响而人心惶然的时候,屡次仗他引导大众的注意走上合理的路线。例如广州失守,学院仓促迁藤县的时候,和前年在乳源立足甫定而粤北突然紧张的时候,全院同人们、学生们都很焦虑,很惶惑,而安定人心,决定大计都多得他的助力。今年五六月之交,我来曲江辞职,消息传到学院,同人们,学生们纷纷发电报,推代表来进行挽留,这自然是一番纯洁的情感的表露,而我很不愿意学生把院长更易看得那么重大,而且也恐怕他们会踏上俗套。六月中旬急写一封信给栗原托他安顿。后来据说他曾扶病出席大会发表一番意见,很得了大众佩服。那时学院像要发生轩然大波似的,而结局很有条理地结束了。学生们却特别自动地爱护学院秩序,丝毫不失常态。这当然是受了他感动。他在校四年,全院同事和教育系以及其他各系的学生对他都无不佩服。我又常遇见由别校毕业而曾受他教导的青年朋友,提到张栗原先生,都自称受他感化很深。他的人格的感召力如此之大,据我观察,大抵因为:他一不沾染道学;二不叫卖什么主义、学说;三大公无私,绝不计较自己利害;四头脑冷静,不轻易雷同附和而也不固执成见;五对于青年有同情的了解。他遇事很能迅速地把握着要领,判断妥当而得体。平时我在校提倡“治事如治学”,其实我自己未能做到,而他确能用治学的态度处世接物,虽没有很多担任事务的历练。他的学养都有高深的造诣,不烦恼,不执着,时时不失泰然的风度。他奉侍七十多岁而双目失明的老母流离迁徙,我每替他担心,可是他并不很焦虑,常常说人的生死是纯自然的过程。
栗原已经死了,我们断不该硬诬赖他还有灵魂存在,我写这一大篇当然不是要对他的灵前曰,而交友之中,认识他比我更透彻的也很多,似乎也用不着我饶舌,我只希冀一般未曾识得栗原的教育界同志知道最近死掉一位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因而分担一份的悲哀!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于曲江。
2019年12月19日下午四点,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列箭老师与校友办蔡一珍老师到北京拜访黎品先生。黎品先生聊到他当年的任课老师张栗原晚年的教学。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入。)
(本文节选自林砺儒:《悼张栗原教授》,《教育新时代》1941年第7期,第14-15页;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列箭老师整理,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