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悦楷《毕加索通讯:论艺术》与何惠鉴《论现代艺术的停滞时期》
——坪石先师文丛(56)
引言: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组团赴韶关浈江区调研考察抗战时期岭南大学旧址,团员之一的省政协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建华女士辩认当时在此就读的学生欧振远,应该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始人和终身名誉教授欧明。返穗后再仔细研读当年岭南学子编写的《大村岁月》回忆录,确认欧振远就是后来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先驱、《汉英中医词典》编者欧明教授,时岭南中学“毅社”同学。欧先生夫人张静娴女士是同班同学,在粤北曲江仙人庙大村校园成为恋人。进一步研究,同为“毅社”另有一对恋人是何惠鉴和董慧徵,何惠鉴先生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学术权威,岭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被聘为美国克利夫兰“东方与中国艺术美术馆”馆长,晚年受聘为上海博物馆名誉馆长。两位大村学子成长为向西方传播中华民族医学和艺术的先行者。
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学生时代何惠鉴就开始发表西方美术研究文章,料想不到的是比何先生低一级的张悦楷先生也发表毕加索美术评论译作。遂推荐两篇被遗忘的文章,对烽火中求学于大村的粤北深表敬意。(许瑞生)

图为青年何惠鉴。(图片来源网络)

图为何惠鉴与董慧徵夫妇。(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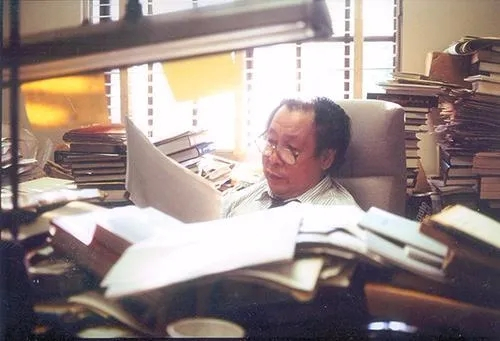
图为何惠鉴先生在工作。(图片来源网络)


图为韶关大村岭南大学办学旧址。
《毕加索通讯:论艺术》
Picasso :A Letter on Art
张悦楷译
英译序:
我们十分感谢Formes编者的好意,把毕加索通讯的节录刊登在该刊一九三〇年二月号之中。该文首见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Russian Review,Ogoniok ;而在这里所登载的,乃是最先的英译。毕加索惯用一种几乎牢不可破的沉默来遮藏他自己,造成他的难以猜测的形貌。于是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使这封信蕴含一种特殊的趣味。
通常我会被认为是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
但我并不找寻,我发现。
有些人想将立体派Cubism转而为“体格文明”之一种。每当他们看见了残缺的身体,自己便俨然起了一种“强者”之感,以为把事物归纳成一个个的四方形便足以表现了“力”之要素。因此,我那些完全合乎逻辑,放进了我全部努力的作品,便被他们用来造出些矫揉做作的东西,而把所有真实都剥削殆尽了。
举例说,某君(原注:一位有名的立体派画家。)便是真真正正“达到目的”的人。
约当一九〇〇年,他的父亲对他说:“孩子,我决定送你到巴黎去学习新美术。”他顺从了。自此,他便在巴黎确定了自己去写作那些几乎和春日杂志(MagaSjn da PrintemPs)内的作品媲美的新美术。
你可以想象出那些所有盲目摹仿我的艺术,摹仿我的作品甚至我的方法的人,使我怎样忍无可忍!
有一天,几个聪明的超现实派的青年画家在我的速写薄内偶然觉了有几张速写和铅笔画,只是由点和线所构成。那是因为我异常赞赏天文学的图样,撇开它们的本体论上的意义不说,它们对于我仿佛十分美丽。因此,在一个明媚的晴天,我开始写一幅画,画上全是许多被线条所连接着的小点,和许多仿佛挂在天上的斑点所构成。我写这幅画的意思乃是预备留待后来,把这种题材加入我的作品之中,作为一种纯粹曲线的材料。但那些超现实主义者!呀!他们真够聪敏!他们竟断定这些图画正正符合了他们的抽象的观念。
我又记得对Jean Coteau 说过一个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故事。有些朋友要我参加国际装饰艺术展览会,这种低级趣味的和令人讨厌的展览——虽然并非完全缺乏教育价值。他们对我说:“你知道,毕加索,你知道你对于所有的建筑艺术是负有责任的。你会在那儿找到你自己,你会认得那些由你自己的双手造成的东西的。”大概他们以为说这种话便是恭维了我。
试想像米开朗琪罗(Micheal Angelo)和他的朋友们一同进餐时,被人用怎样的辞句去欢迎他:“我们刚巧定制一个认真美丽的文艺复兴式的食橱,这是由你的‘摩西’(译者注:‘摩西’为米开朗琪罗杰作之一。)启示我们的!”请你想想米开朗琪罗在那种情形下的脸孔。
从同时代者的作品中不断抽取其灵感是多么的愚蠢?每当我发觉自己被人摹仿时,总觉得有些近乎肉体的痛苦。
装饰艺术和一幅画的制作,至少是对于一幅画架上的制作,并无相同之处。前者是功利主义的,而后者则是一种高贵的工作。如果你以为一张安乐椅的意义是它有一个靠背可以坐得舒服,那么它只是一件器具,它并不是艺术。
当一九〇六年,那天才的HerPinies,塞尚(Cozanne)的光芒到每一角落。构图,形式对立和色彩节奏的艺术,很快地为人所知。我因此发生了两个问题。我知道了在真实地表现那对象之时,绘画本身是单独地有一个内在的价值。我会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不是事可表现我们所见到的东西而不表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因为绘画自有其本身的美,所以一个人可以创造一种抽象的美而置之于图画之中。许多年来,立体派画家除了只是去写画之外,并无其他目的:为绘画而绘画。他们除了绘画之外,把每一种并非产于那主要真理的成分都丢弃了。
有一位名叫 Princet 的数学家,他在我们讨论美学的时候,时常被提起的,他有意创造一种特为画家用的几何学,不幸他的意思已不是新发明,因为达文Leonardo Da Vinci 的几何学,甚至在任何学院也早已采纳了。
颜色之有用,只在乎他是体积的构成原素之一。人人都觉得同样大小的平面,白色的往往看来较大于黑的的。这只是原则上的甚至是幼稚的说法。然而,这却不免被一般傻子立刻使尝试去引申为绘画的普通的法则和定律,而他们便可以恃这这些定义来对我解释艺术了。
我以为一种画永远不会是一个终点,也永不会是一个目的。它宁可是一种愉快的遭遇,或者是一种经验。在形式的规范里,色彩构成了量的标准。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困守在科学的几何学内的意思,但仍有许多自告奋勇的观察家,却甘于牺牲他们自己,去循着这途径作种种的研究。多大的错误,而又多么应该淘汰的这些弱者呀!……
被他们自己的作品愚弄了的立体派画家们,尝试去制造一个理论的断头台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立体派缺始终没有一个方针。需知道一幅画可以代表外在对象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代表他的外表形貌而无伤。
归根到底地说来,一个人永不可抄袭自然,也不要模仿自然。让我们由想象来还事物以他们的真正的面目,所以说绘画想摈弃自然化这一点是毫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应该由自然转到绘画。有许多作家把太阳转变成一个黄点,但亦有许多画家由于他们的艺术和聪明的帮助,把一个黄点转变成太阳。
取自自然的各种特点,可以给予绘画许多变化,这就是我们怎样去接近那些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念,去表现事物的自然的外表的大师们的方法。
我们信任所有绘画的来源之中,人们必定时常发现到很主观地组织好的幻觉,或者得到灵感的启发如同R imband 所得到的一样。
我并不注重主观。只是一切都为了客观,尊重客体。
永远不要使你的思想在外观上或次序上有所混乱。
我们现在都知道所有的艺术都是不真的。
艺术是一个令我们接近真理的谎话,至少这真理是可以被人了解的。能够找到方法去说服群众的画家们,则他们的谎话便是真理。
我觉得很难明了“研究”这二字的意义,并且我也不相信它们有什么意义。谁也不愿意去跟随一个眸子放在地上而希望幸运会丢一个钱袋在他脚下的人。并且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也就完了。因为即使我们本来无意得到,但总会由此而赢得(就算不是尊敬)公众的注意。
我尝试去绘画我所有会发现的而不是我所搜寻的。事实上,目的在结果中并没有什么影响。西班牙的谚语说:“爱情的证明乃是行动而不是言语。”“研究”这观念使有些画家钻到抽象的牛角尖去。也许这就是近代艺术的重大错误之一。“研究”的精神毒化了所有那些不明白近代艺术的真义的人。他们尝试去画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是艺术所不能表现出来的。
一幅画所表现的往往超过作者希冀之外。而作者竟预期那些出乎意料,不可预知的结果,那实在是愚钝。
一幅画之产生,时常令人感觉来得很自然而不能事先计算到的。
普通人把自然主义当为近代艺术之对立。但是,几时有人看过一件“自然的”艺术作品?
自然与艺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
艺术给予我们以表现我们的概念和睿智于一个绝对形式中的可能性;而自然则永不能如此。从距离自然很远的初民艺术,乃至大卫(译者注:Louis David 生于一七四八,卒于一八二五,法国名画家,为古典派的领袖。杰作有“拿破仑戴冠式”等),恩格斯(Ingres),甚至Bongueress 所有描写自然的画家,都清楚地知道艺术就是艺术而永不是自然。站在艺术的立场而言,不论抽象的形式也好,具体的形式也好,都并不存在:这都不过是牠的或多或少的因袭的解释而已。
立体派与其他绘画的各种派别并无分别。牠们都为同样的原料和同样的原理所统治。
许久以来,立体派被人误会,甚至现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而那些愚昧的批评也会损其价值。譬如我不懂德文,所以德文之于我只是许多白点黑字。但是却不能因此而下结论说德国语文不存在。
立体派不是一种新艺术之收获或萌芽:它代表了历来绘画形式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必须要明白的是,这些形式有其独立生存的权利。
要是立体派目前还是初期,那么立体派的新形式随后便会产生。人们曾经用数学,几何学,心理分析学去解析立体派。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文学而已。立体派是追求那能够自我满足的造形艺术之终极。为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定义说它们是表现我们所有的理想与及我们眼睛在构图和色彩所容许的可能范围之内所看到的一切的方法。这是怎样一个意外快乐及发明的永不枯竭之源泉呀!
Henry Rousseau (译者注:后期印象派四大家之一)并非特例。这不过是心智完善的程度特优的情形而已。当我第一次有机会看他的画时,使我感觉万分惊异。有一天,我沿着烈士路Rue des Martytg 走的时候,看见一位古董商在他的店内,沿着墙壁把许多油画挂起来。有一副肖像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女人的头部”,充满了庄重和锐敏的眼光,澄湛而稳定:这是法国女人的眼光。这幅油画是很大的。我向他问问价钱。“五个法郎”,那个人说,“如果你拭净它,你大可以在上面再写一幅画的。”
那是法国学派中描写最真确心理的肖像画。
我很感惊讶地去看“进化”这字怎样被人运用和被人滥用。
艺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凡艺术不能使自己证实其价值于当时者都永远不是东西。希腊与埃及艺术并不属于过去:它们在今天远较昨天为有生命。变化并非进化,要是艺术家改变了他的表现方法,这不是说他已经改变他的宗旨。每人都有权利变化,即使是画家。
我时常为自己的时代而工作。
我永不忧虑研究的精神。我表现我所见到的。
我不用“沉思”来麻烦自己,亦不丢自己人“实验工作”。
如果我有些东西要说出来,我便用似乎对于我最自然的态度来说。
过渡的艺术不会存在的:只有好的与坏的画家,如此而已。许多好奇的新闻记者和艺术的爱好者,来探访我们,都怀着从我们身上抽取出教条式的真理或定义的心理,以为那些教条定义便足以为他们解释我们的艺术,而把它们教学的价值——一种我无条件否地否认的价值——放在安慰之中。我们是画家。是不是他们想我们都变成真理与格言的翻制者,而注视着市场呢?
不错,恩格斯和Delacroix 的文集是出版了。这事使我们战栗。Delacroix的什么思想可以和他的Sardan APalus 这一幅画相比呢?
什么是艺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该小心不要泄露出来。
我并不找寻,我发现。
译自 Creative Art
按:毕加索为现代立体派绘画开山大师,天才横逸,成就包括多方面,故抽象派构成派等新兴艺术亦奉他为大师,然在本文中则毕加索对此种荣耀似大感不耐烦,译成中文,似以此为首次。
《论现代艺术的停滞时期》
何惠鉴
作者本拟写一论文题为“现代艺术之纯粹主义的倾向”,本文为其引言。共余第二部份拟论及现代艺术之思想背景。第三部份拟从音乐,美術,及建筑等范畴分析现代艺术之诸倾向,而综合其基本相同點名之曰“纯粹主义”。第四部份拟从温克尔曼来以之古典主义理论重新加以估价,并根据纪德及卢那卡尔斯基诸人之意见,而指出现代艺术之可能出路为唯理主义与触感主义相调和之新古典主义。结论似属鲁莽,盖亦读书后感之类糅杂而成,聊作尝试而己。惜因时间仓卒,未及完成,致令本文有残缺之感,至以遗憾。
“欧洲失踪了”!这一七九三年的老话,在这个世纪初又再度地响在每个人的心里。岂止欧洲,岂止那些以野心和生命来解渴的人,简直连整个人类的心灵都因为战争而枯萎得要死了。人们虽然已为自己的生存弄得十分惶惑,然而悲剧至今还未见有闭幕的样子,除了愚蠢以外,这“世纪的情人”似乎还拥有大量的追逐者。尤其是艺术,要想在这恐慌和饥饿的社会里找寻一点滴新鲜的活力,其结果却只可以寻出一个谜:一个沙漠可以用来饶另一個沙漠吗?正如它所以开的花所有都是不可想像一样,我们试走入那奇异的园里去看看那些花的名字:那個以战争为无上地纪念碑的美底未来丰主義,那个以触觉为天国的锁论底触感主义,那个想把无线电的电波也画了下来的同時主义,那个自称为佛教底亚美利加的表现底大大主义(注一)......一切都不可思意得骇人,要是再说下去,我恐伯那些在威士敏斯德寺安息着的灵魂们第一台群起争取安宁了。
然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却应该有正视这个“停滞时期”(注二)的勇气。所谓停滞时期,就是当某个社会升腾到了它的顶點,由于本身的矛盾,于是不可避免地衰落,而接着这衰落之后,一种新生的飞跃的进步在酝酿着;在这结束与开始之间,那密云不雨的时代全被窒息而又混乱的空气所笼罩着。腐朽的气息和暴风雨的前奏,吹逼每个人的心里。而艺术,则正如雪莱底西风曲中所说:是这时代底预言的喇叭:把乾枯的死叶,投向那不减的炉火之中。
从这一观点,那么我底意思和诺尔度Max Nordau诸人的世纪末底变质说degeneration(注三)之相左是显然的事,诺尔度以医学和精神分析学为根据,说世纪末的特征,是由于都市所生的疲劳而引起人类的变质。于是反映到艺术出来,便形成了怀疑,激情、忧郁、静寂主义quietism和神秘狂的倾向,这种说法,在萧伯纳的“艺术之健康”里曾经受到大大的挖苦。我们且不必理会萧伯纳,亦不必把这种人性分析底自然科学的基础估价得太低然而在艺术和科学之间,不可怀疑地是有着一种虽以相互解释的空隙在,自然主义想消泯这空隙,结果是被这空隙所消泯了。即使我们承认近代科学把共同经验与特殊经验拉近一点的努力(注四)。然而但从官能的立场来意味着近代艺术,这却是一个最易犯的错误。近代艺术虽则极强烈地散布着官能的芬芳,“但却是从官能终了之处开始的”(注五),我们最好看看立体派大师毕加梭自己的话(注六),看看他怎样不能容忍那些想把立体派转为一种Physicai Culture的理论,于是便可以明白“变质论”和所谓世纪末的艺术之间,是存在着如何一种距离了。
我们假若稍为退步,而转向到诺尔度底生物学的方向来,于是达尔文的话便不得不重新提起:“生存于社会的动物间,自然淘汰将个体加以改变,庶使他能效力于大群。可是,也要该大群能从物种改变得到益处。”如今假设现代的个体已经变了质,但大群从这种变质里得到了什么益处呢?拉马克已经证明:个体之适应环境,固然x客观条件x诱导作用在,而更主要地,是自己是有着一种目的意义性。(注七)这种内在的目的性,使我们不能想象在现代这种超越官能的客观条件下,人类竟会选择那些并无益处的变质。因此诺尔度是把那相互的因果关系只截下一段,于是跳过了进化而终于与进化论为敌对。我在思索这是问题之余,觉得在同一的出发点上,卢那卡尔斯基底实证美学上的x就应该是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人类是靠着对于外在底现象的许多复杂的反应x而支持自己的生存的”(注八)。诺尔度的所谓变质,无宁说是现代人为了适应他底社会的内容,而显现于复杂的内在底过程之后的各种反应,而此种反应,则后定于生命和他周围的存在如何地保持均衡这努力之上。原来在生命底一个假设的常数中,在积极和消极两种“生命差”的存在(注九)。现代生活底矛盾和复杂,迅速的变化与不安定,破坏了个体的均衡。于是个体的反应,便以一种消极的形式出现。但如果社会的内容改变,则个体无疑地必依照最小限度底精力消费的原理,而重新与环境调和。这种推理,在表现上约略类似布哈林的“均衡论”,即原有的平衡状态为正命题,平衡的破坏状态为反命题,在新的基础上的均衡底恢复为合命题(注十)。所不同者,是布哈林从外在的矛盾出发,而我们则从内在的反应出发,而略过了机械论的障碍。这比较诺尔度更为平易的道理,但人们却宁可相信更复杂而较新奇的——这或者也是现代人底特征底之一。
我不知道人们彷徨呻吟于停滞时期这一个荒原之上的时候,可会发觉在那些死叶和青苔之下所泛溢着底新鲜的气息?这个时代无疑地是一首挽歌,一首凭弔自己的挽歌。但却并非向生存闭眼,像死亡低首。定命论的短音阶不能作为基调而支配着。那只是果实烂熟,而让位给新的种子那种无可奈何底悲伤。那些对生命最厌倦的,必定也是对生命最执着的。因此真正的厌世主义不发生于沉闷窒息的时代,却往往发生于生命最自由最放任之际。反之,我们也可得到同样的推理。这种现象,差不多每个停滞时期都如此。我们非常容易地便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两个例证:譬如中世纪和巴罗克Baroque时代。(注十一)
中世界的开始,照一般历史的分法固然应该稍后,但要是站在文艺的立场,我以为不妨大胆地把它提前到纪元三世纪。当那个美丽而年轻的女郎夏波霞(HyPatia)在基督教僧侣的手中结束了她底悲剧生涯之时。自此以后,新柏拉图学派底最光亮的星座陨落了,而希腊精神的最后壁垒遂告消灭。
Pania dead!——Great Pan is dead!(注十二)在这悲哀的背后同时也正藏着中世纪的欢欣。
然而,即使在那黑暗时代底最彷徨的几百年间,当禁欲主义走到了悬崖的边缘,而除去了利己主义(Domatism)和形式主义(Formalism)底空虚的外壳便等于一个零之时,那人间本位的异教徒流却无处不隐然抬头,除非我们掩耳不闻法国南部的Troubadours和德国的master Singer等行吟歌人那种赞美肉的欢乐的诗歌,或是完全忽略了关于浮士德和维娜斯山府底怪尘离奇传说,我们实在无法否认一种燃烧般的思想正在发光着。甚至在最隐秘的一所巴伐利亚的僧院里,那最近发现的一本拉丁诗集抄本(Carmina Buraru)(注十三),也惊人反动地以青春美丽和恋爱来装饰这个落寞的中世纪。在这一点之上,我们实有理由说文艺复兴不始于但丁,而始于那些停滞时期间的灵魂。
至于巴罗克,它所发生的时代正式霍布士——斯宾诺莎底唯智主义作为社会内容之际,所有的哲学全建立于一个真空的系统之上,仿佛与生命,热度和呼吸完全隔绝。而那种坚决顽固的逻辑则苦苦不舍地去穷追思想:于是由因果的观念一直到毫无生气的自动论地步;身心的差别一直到了身心之间毫关系的地步;控制情绪的愿望一直到了无知无觉的地步;总之这种纯粹理智的产物,前后联贯,彼此相因,以致结果把思想的对象完全废弃,把它们破坏,分裂,终至于以为他们未尝存在。到了最后,所剩下的真理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公式,甚至连自己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巴罗克之兴起,正是处于是样一个冻结的时代里。如果我们通过了诺尔度的看法,则巴罗克的病态必远较今日更使人惶惑。文艺复兴所厅厅于使人性复归于秩序与和谐的努力,巴罗克则唯恐不至地把它们收藏在一种谜样得混乱之中。因此自十八世纪至今,人们总习惯把它看作一种繁琐的,不自然的,出乎常态之外的,(或许就是所谓变质的)艺术品。“在其无意义与莫名其妙之点,殆和十五世纪初叶的三十年战争不相伯仲”。(注十四)
但可注意的是:三十年战争为了要改变某些势力而流血,结果则为了流血却使这些势力更加稳固了。而巴罗克呢?我们不论在提起这名字的时候如何掩抑不住一种厌恶之情,或竟较厌恶更甚的轻蔑,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它和前者之间大有差别,那就是:巴罗克代表着某种新生。
也许从巴罗克的不自然性看来,生物学或精神分析学可能找到一条相当平坦的路。(其实在是否不自然这一点,也大有讨论的余地,见附注十五)然而,生命却往往滂x迸发于桎梏里,而在乐园中则亚当也有寂寞得要逃走的一日。因此安特烈,纪德说:“艺术因束缚而生,因战斗而活,因自由而亡”(注十六)。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停滞时期的艺术都会因此而得到它们的荣冠。我并不是说这个世纪末的病态竟能给现代艺术以多大的活力,因为艺术与其环境之间往往是一种反射的关系而不是取予的关系。我只是说每当一个艺术的颓废期,人们总是把它们放逐到自然法则的死亡的王国之下,做一个不二之臣。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艺术与自然在地上为匹敌,正如规律与放纵在艺术上为匹敌一样。是的,他们并没有错,艺术拥抱着自然,并且紧紧地搂住他!不过那却要用那有名的诗句来做注脚:
“我拥抱着我的情敌,可是为了要闷死他。”
在自然凋残的地方,艺术仍欣欣向荣。原因是艺术的价值并不在自然,而是在睥睨一空的人性的欢欣,力的美,与生命的怒潮,因此那伟大的勃阑德斯在漫游拿不勒斯的时候,也禁不住要对罗柯柯(注十七)的巨匠贝尔尼尼(Bernini)底雕刻低首:“他们是如此伟大,当我们理解它的时候,心中所被燃起的热情是在远较许多近代作品强烈得多了。这些现代的雕刻家虽然没有产生过什么歪曲的作品,但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独创的作品。”(注十八)
在今日法国卢森堡美术馆里:陈列着现代大天才罗丹於一八八七年的杰作——青铜时代。这雕像是一个远未完全觉醒的青年,手足的肌肉仍然十分松弛,几乎摇摇欲扑地支持着他的身体。但从他的眼光飞扬看来,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身躯逐渐稳固,颜面向着天空,双手紧张,似乎想要摇醒自己的惺忪昏昧。很显明地,这雕像的主题是表现从沉睡至精力的活跃的通路。(注十九)我们如果把它和米盖朗琪罗的“创造天地”底中亚当的像来比较一下,那末更禁不住要惊叹在那主题背景后所泛滥着的趣味:人类觉醒了!这是在有史以来人性的第一次觉醒,也是理性对兽性的第一次胜利!
我不知道这二十世纪的停滞时期还要昏睡到什么时候,然而夜色已经动摇,曙光不远了。而我们诸如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里所说,“今日我们所丢弃的,明天会重新加以膜拜;而往昔所膜拜的,今夜我都把它们烧毁。”
附注
(一)玛察(I Matsa):“现代欧洲的艺术”第一张第二节——“飞机,因为它的运动是非常出色(美的原理),又因为将人们从视野的狭隘里解放(道德的原理),所以是好的。战争,因为它的运动是无上地纪念碑的(美的原理),又因为将人类从平庸的消极性里拉开(伦理的原理),所以也是好的。”——这是未来主义的理论。
触感主义(Taktilism)——是触觉器官的艺术,出现于未来主义的颓废期。它的首创者玛里内谛把初次的作品取名为“从苏丹到巴黎的旅行”。这是一个表格,在里面放着种种可以唤起非洲的沙漠,海,饥渴,铁路,以及巴黎的街道底印象的东西。
同时主义(Simultanism)——所谓“超时间,超空间的综合艺术”。例如:巴黎的广场上,退伍士兵在徘徊——在维也纳,修补军靴的人成为百万富豪了——把第十个香槟酒的瓶,运到卫军们的大腹下......之类,便是触感主义者的诗。
关于大大主义(Dadaism)——Riehard Hulsenbeek解释说“大大云者,是佛教底亚美利加的表现。他因为能过够沉默,所以是喧嚣;他因为是平静,所以是行动者的”
(二)卢那卡尔斯基:停滞时期的天才梅里美
(三)诺尔度“变质论”第一章第一段:“世纪末者这一简名词,包括着近代诸现象的种种特质与其基本格调(x内在倾向)的两面。......法国x它底真正产地,而巴黎是一个最能代表它的地方。”
(四)H·Dxxxle:Science and Experences
(Chp)
Barnhard Baving:现代科学的分析(第二册第四编第八章)
(五)Herbert Reed:今日之艺术(第一章第六节)
(六)W H Wright Modern Painting:(chpt.II)
(七)王特夫:生物进化论之理论与批判
(八)卢那卡尔斯基:实验美学的基础(第一章)
(九)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第五章)
“生命差者,是从生命的普通的规则底长流,脱了路线的事,无论这是由环境的不惯的作用直接地所惹起的,或是由什么内在的过程所惹起的,结局都是一样。”
(十)布哈林:史的唯物论
(十一)佛里采:艺术社会学(第八章)
巴罗克式为十七世纪之作风,Baroque者,原系宝石商人之用语,盖云Bizaxxc(怪)xxxe uxa(不规则);在反复凌乱之中,以design作奇肆之怪相,以显…。在作风上,古怪,起义,歪曲而眩目迷人。尤其在建筑上,指流行十八世纪全欧之样式,与当时法国之装饰。此风起源于十七世纪,由文艺复兴式而来,在路易十五治下法兰西,更以奇恣之风的放荡色彩,渐渐发展而为罗可可式。巴黎之St Sulpice等及凡尔赛宫可为其代表。
关于巴罗克式及罗可可式霍x斯坦恩论之x精,除见于一艺术与社会中者外更有“罗可可论”,论巴…克克精神等著名论文。
(十二)Mrs Browning:The Dead Pan
关于希腊精神死亡的事,有一著名的传说:在基督圣诞夜行经泰兰敦海峡的旅人,总会听到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悲论说:“大般恩神死了”(The Great Pan is dead!)
所谓般恩神者,是指希腊x由山林之颠,代表异教底自由放纵的一面,他时常出现于黎明的水x或朦胧的夜里,那种夜,是纯粹希腊的夜,也正如勃兰德斯所说的:“是恋爱的夜,是暗杀的夜,是暗藏着狂欢与罪恶的夜。”白朗宁夫人的诗,大概也是出自上面的传说。
(十三)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第三章)
此诗集一名“流浪者之歌”,有意西蒙士的英译本名曰“醇酒,妇人与歌”(Wine Woman and song)
(十四)E·Friedell:现代文化史(中册之一第一章)
(十五)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如果有人说巴罗克是自然的常态的艺术,那么换来的必定是一场耻笑,或者被人看作一个认真而可怜的笑话。
但福利德尔却持相反的论调:他说:“有一点是不能驳难的,就是巴罗克的艺术要比文艺复兴的艺术自然得多,”这儿得所谓自然,妥协一点来说,就是不自然中的自然性,一切停滞时期的艺术在其精神深处都蕴藏着这一点无可比拟的天真。
事实上,巴罗克的口号的确是“自然”,若以反抗文艺复兴的精神来看,则巴罗克便是这种要从束缚中解放的本能,仿佛想震羽而飞的热情,与及对色彩和形式的饥渴。文艺复兴想把艺术带回单纯与统一之境,结果是带到一个沙漠中去了。这些在佛罗x斯的废墟里使七十岁的歌德目瞪口呆的建筑和雕刻,其实便是这茫茫沙海中的少数绿洲,然而歌德却对此掩眼。自此而降的巴罗克时代,不但以一泻千里的欲望要在形式上归返自然,并且在内容上也要归返到那无拘无束的汪洋,而以摆脱一切权威的桎梏为了其时代呼声。尤其重要的,就是“人”在艺术中的地位巴罗克实远较文艺复兴为显明:文艺复兴期只有少数的杰作能够在非自然的题材中有人性的光芒作瞬间的闪灼。然而,巴罗克即使在他底极后期中的域多,Antonie Watteau(1648),在内容上也深深地侵入了精神生活的领域内。譬如那著名的“船渡手卷”,使人如听莫扎而特底室内乐一样,那说不出的没,就正如那反复着可怜的旋律底横笛。而在优美与和谐的背后,有轻轻的一缕哀愁在流行;这种哀愁,正是那没落的布尔蓬王朝的哀愁,也就是作为“人”的巴罗克,在那孱弱的形势下发现了自己的好梦觉醒。但这样也只是巴罗克的一面。巴罗克所心爱的题材,在其野蛮,歪曲,丑恶与疯狂之处,既为文艺复兴式所不屑,同时也给与现代人以一个最有利的攻击材料的,我们都可以加以一种好像矛盾的辩解,这就是:因为是它如此不自然,所以才能如此自然。因为在自然界中,平凡无奇的东西并非常态,反而奇形怪状的,身心都有病态的,或者不依照正常法则存在的,那倒是自然界中的普遍现象。因此自然云者,严格地说只是一个主观的名词。每一种新的趋势都深信不疑底自以为比较以前的趋势更近乎自然,更近乎真理,无论它是采取怎样的形式来表现,但其动机总不外想提高对现实的自觉。因此我不怕反复着这同一的话:任何永久的艺术,都从不恃自然而取得它在时间中的地位。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巴罗克所以如此装模作样,如此舞台化的缘故,是有着她自己底特定的思想背景。这种思想,是以一种假设的哲学建立它的基础,又从一种假设的系统演绎而取得其生命。无疑地,“假设”这名词仿佛自有史以来便被一般人忽略,但如果它从不存在,那么今日的世界必定不可想象。因为宇宙间本来无奇不有,不仅有有害的真理,而且有有益的错误。事实上我们时常发觉,唯有经过这种虚构,我们才能在现实中把我们的位置决定,一切的逻辑才能由此出发,一切的价值才能由此评价。我最近在H G Wells的“世界纲”里看到一个有趣不过的例:在基督教中关于亚当夏娃和毒蛇的故事,其实出自古巴比伦的神话,而基督教则让此为己有,从而开始自己的整个体系,而二千年来的教徒,则以此来建立信仰,并不惜以热血头颅来巩固这个假定。于是人类便在这沙上的历史宫殿,渡其悠久的岁月。这样的例如果有还人觉得可疑,那么科学必定较为有力:我们都知道“真理”之于科学,不过是一个假定的鹄的,譬如无穷小的“数量”其x矛盾与莫名其妙,正如没有体积的点,没有x度的x和没有内容的空间x为笑话一样。然而科学却藉此而窥自然的奥秘,把人类拯救出纯生物学上的名词之外,所谓巴罗克精神,它的秘密便全尽于此。
原来在中世纪的时代,一切都是真实的,神圣的;这个世界也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和人类的信仰全无间隙。到了唯理主义却把这种信心倾覆了,因之也倾覆了实在。后此的几个世纪,无论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完全是想对这答案给以一种反抗的奋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否定的方法出之,巴罗克则以唯感主义的方法出之。然而在唯感主义和唯理主义之间,彼此相成之处实较相斥之处更多,于是便采用另一种花样,设法去愚弄现实,冤枉现实,努力使现实降到第二流的地位,或则拿不严肃的态度去看现实,只以现实为游戏(这是艺术的形式),或简直认为现实为虚妄,为谬误(这是宗教的形式);而他们则表面上则模作样地好样相信这“现实”为真似的,其实心里却不是这一回事。——这便是奇怪的巴罗克态度。
这种态度和唯理主义似乎是一种矛盾;但这种态度的存在,唯有从笛卡儿所谓“理智如…之光”底艺术似的坐标系统中才能找到最有力的解释,这却是更自然不过的矛盾。笛卡儿的最高原则是“一切都可怀疑”,但只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是我们怀疑一切的这个怀疑。从这假设出发,一条路便走到“我思故我在”,另一条路便走到“我觉故我不知我在”。因而他说:“当我感觉这世界之时,我简直寻不出一个特点,可以把醒境和境正确地分开。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简直茫然无措,不知我是否在做梦,抑或是醒着了。”从几句话里,笛卡尔忽然把他的假面具揭开,而露出一个巴罗克的真面目——巴罗克的真面目,便是假设这原来的自然为不自然,于是他们的不自然便成为自然。
这样地说下去,我们未免在一些过于抽象的概念上盘旋得太久了,只有最后一点不免于言的,就是刚在脑中闪过的歌德在“浮士德”里的瓦曹几司之夜——
“从前有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
两个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枝去。
自从天国到如今,苹果滋味你深喜,
我亦欢喜不自持,我的园中也有此。”
这委实是十足的巴罗克内容,但却自我抑制在如此单纯,如此明净而统一的形式中,这真是可惊叹的古典之域!法国近代派大师之一的雇诺(Gounod),在为这首诗所写的歌剧中,浪漫精神是表现得很够充分了,但在他的旋律里却仿佛缺乏了一种“内感的生命”,仿佛那放浪的内容和拘谨的形式还互相逃避着,在这种地方,最近的“短动机”和“多调性”的新倾向音乐反而富于暗示性的力量。
我所能为现代停滞的时期的艺术想象一条路,极压缩地来说也正在此处。
(十六)Andre Gide 戏剧的进化。
(十七)佛里采:艺术社会学(第八章)
罗可可式是十八世纪法国建筑的作风,繁琐与复杂的装饰细工为其特点,此种样式为巴罗克的继承,法国的Zwinga Pajaco 可为其建筑方面的代表。
(十八)G. M. C Brandes :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第一卷)
关于贝尔尼尼,近代古典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温克尔曼在他给Uden 的信里说过:“现代的人若与古人相比,全是些骗子,至于贝尔尼尼便是一切骗子中最大的一个。”
(十九)罗丹:美术论(第四章)
(注: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入。)
(本文由阿瑞推荐,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熊灿坚 何洛曦